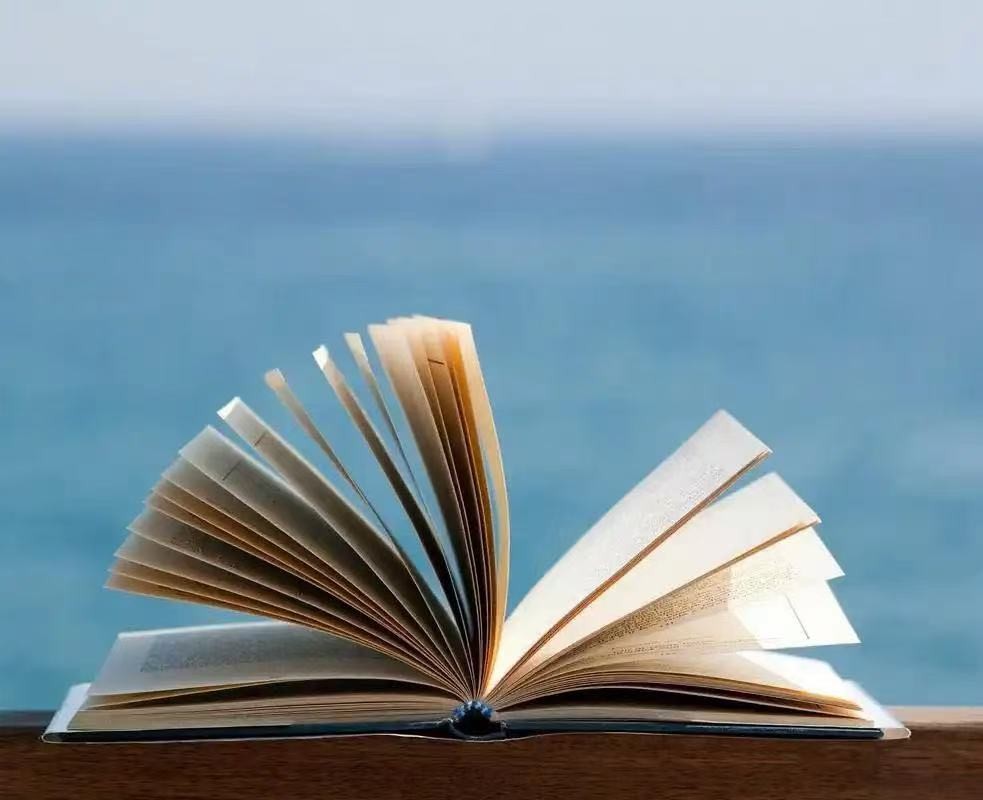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智慧就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传承下来
---瑞秋.娜欧米.雷曼《智慧书桌》
我的故事
--- 心怀梦想,重新上路
原文摘要
三十多年前,泰瑞克 似乎一切正常。他符合我的所有期望,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比如说,四个月大的时候 ,他开始抬头四处张望。当时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并珍藏至今,因为它酷似我小时候 的一张老照片。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开始爬行。我看着他那副样子,感受着他那股兴奋劲,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中。当他在屋子里随心所欲到处爬的时候 ,眼睛里是闪着光的。这时候 我就得给他一点儿安全保护了,比如说把他从楼梯、壁炉边引开。
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可以扒着东西站起来了,小脸上满是自豪。他面带笑容,环顾四周,心里盘算着要从哪个看起来比较好玩的地方出发。没几周他就能扶着走得很溜了,只要有空他就扶着家具到处走。那个时候 ,我抓着他举过头顶的小手跟在他的身后走,是我的一大乐事。
泰瑞克 第一次抬头
转眼就到了他的周岁生日,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独立行走。我还记得他笨拙地、蹒跚着迈出最初几步时脸上的表情:先是紧张害怕,转而化作成功的喜悦。我真为他骄傲,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为他欢呼、加油。后来在很多次公众演讲中,我都喜欢展示他的这张照片。
泰瑞克 周岁生日那天学会走路
到一岁半的时候 ,他开始说话,还学会了好几个单词。一直到那时为止,他应该到达的所有发展里程碑,全都按时到达了。我憧憬着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开始打少年棒球联赛,而我则会在球场边带着一脸自豪为他加油喝彩,看着他成功守球或者轻快跑垒,就如同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从少年棒球联赛开始打,一路打到成人垒球,虽然球技不算高超。我将会注视着场上的泰瑞克 ,一如当年我父亲注视着场上的我。我想象着,当泰瑞克 长成一个大小伙子的时候 ,我会跟他聊社会公正和体育赛事。我们的关系会是亲密而温暖的。我会耐心回应他的各种需求,我要当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爸爸。
1981年5月,泰瑞克 一岁半的时候 ,因耳道感染而接受治疗。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他开始变得烦躁、退缩,动不动就哭,晚上也睡不好。我忧心忡忡,晚上醒着陪他的时候 更是如此。我的大女儿(她希望我为她保留隐私,不提及她的名字)正好也是这个月出生,所以一开始儿科医生以为泰瑞克 是对妹妹的到来产生了情绪反应。我当然希望医生是对的,但我仍然感到很害怕。
渐渐地泰瑞克 不再说话,不再玩周岁生日时收到的那些玩具,比如我父母送给他的带螺栓、螺帽和各种工具的工作台——跟我小时候 玩的那个工作台一模一样,这也是我父母送他这个礼物的原因。他开始玩一个里面有鲜艳彩珠的摇铃,似乎对它无比痴迷,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却对身边的一切都置之不理,包括他刚出生的妹妹。就是从这时起,他对物越来越着迷,对人越来越冷漠。直到多年以后,在2011年美国自闭症 协会大会上,我才终于了解到,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阿米·克林博士和他的团队已经研究并记录了这一过程(Ami Klin et al., 2002):后期被诊断为自闭症 的儿童,一开始对人都是有着目光注视的,但是其注视的对象会逐渐由人脸转为物体,这种转变通常在婴幼儿期就会发生。
泰瑞克 在玩我父母送给他的玩具工作台
当时,大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新的激动。人生似乎圆满了,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持续多久。我开始紧张焦虑,怀疑会不会是我和孩子 他妈做错了什么,才造成泰瑞克 的这种状况。同时我又不断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一瓢冷水就劈头浇来。新本领带来的快乐不见了,我可爱的学步儿不见了。只要拿走摇铃,他就烦躁生气。他的生命,原本带给我无限喜悦,如今却变成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每天下班回家看见他,我还是会很高兴,但已经找不到从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了。他还是喜欢被抚摸被搂抱,但他会转过脸去。他更喜欢的还是那个摇铃。我多么渴望泰瑞克 能与我对视,能开口说话。
泰瑞克 两岁的时候 ,我趁学校放假陪了他一个夏天。因为儿科医生说,泰瑞克 或许只是需要多点时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建立眼神交流,我想尽了办法。我把他放在秋千上,站在前面推他。我试图抓住他的目光,哪怕是一秒也好,可他总是把眼睛转向一旁。他总有办法回避一切交流,包括目光接触。
那种感觉就像被当面拒绝。这让我格外挫败,因为我原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帮助他。当时我正在一个助学项目中教补习阅读与写作,在工作中我可以帮助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大学生,但我在自己儿子身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却没有任何作用。最终,我还是学会了放手,学会了用别的方式去交流,但那是又过了两三年,他被确诊为自闭症 之后的事了。
在泰瑞克 三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 ,现实已经摆在面前:他没法去上正常的幼儿园。光是不会说话就足以证明他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 ,但这个事实太令人难以面对了。我和他妈妈带他去了一所接收特殊儿童的幼儿园,但他在那儿都没法待,因为他一刻也坐不住。那家幼儿园的心理顾问认为他听力有问题,因为他被叫到名字的时候 总是没反应。在他的建议下,我去考察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一想到儿子可能走到哪儿都得戴着助听器,我的心就直发抖。
我不知道他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对自己说,他只是会与众不同——只是不同而已。那些日子,不知道见了多少专家,跑了多少特殊学校,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检查结果,然而没人可以告诉我,泰瑞克 究竟为什么不再说话。
一位专家在他的耳朵里发现了可能阻碍他听力的积液,于是我们开始对他进行药物进行治疗。一招制胜的希望似乎出现了。脑干检查显示他的耳朵功能正常,但无法判断他是否理解语言。积液清理掉了,但他依然用哼哼唧唧、咿咿呀呀、哭哭啼啼来表达自己。他总是翻来扭去地想要挣脱我们。那天夜里,我梦见他的咿咿呀呀又变成了话语。
满三岁的时候 ,泰瑞克 上了一个早期干预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早期干预并不是从一出生就开始,而是到了三岁才开始。他是学校里最难管的孩子 ,始终需要一对一看护。如果不看着,他在座位上连几秒钟都坐不住。只要有空,我就会去陪他,协助他的老师。我不停地追问他的语言治疗师,为什么他还是不说话。她给了我一本美国自闭症 协会的小册子,上面用火柴人图画描绘出自闭症 的征兆和症状。我的视线一片模糊,已然看不清那些文字和图画。
最终泰瑞克 被诊断为广泛性发育障碍。1984年儿童自闭症 的诊断率是万分之十二(Gillberg, Steffenberg& Schaumann, 1991)。在他出生的医院,对他进行评估的专家组在诊断中使用了“类自闭”和“智障”这样的字眼。我一开始木然,继而大怒。他们似乎对我儿子不抱任何希望,但我如何能放弃?他们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头,我的脑袋一阵阵作痛,我想它一定是要炸裂开了。
社工当时是这样宣布消息的:“难道没人跟你说过你儿子是自闭症 ?”——有这么跟家长 普及自闭症 的吗!
我开始逃避。自闭症 是一项严重影响生活能力的终身缺陷 ——这样的话读起来太令人痛苦了。我孩子 的大脑有严重缺陷 ——这样的结论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们还说,对泰瑞克 而言,与旁人或外界交流,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件事。倒是想跟人谈谈,但话到嘴边却总被卡住,尤其是“自闭症 ”这个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时不时地,我的担忧又会毫无防备地冲口而出:我儿子都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半夜里,我泪流不止。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我。专家、亲戚、朋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跟许多父母一样,我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找到疗愈的办法。我们试过另类疗法、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无麦饮食疗法。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给我带来的累累负债,是我对泰瑞克 寄予的康复梦留下的纪念品。在我试遍所有能找到的疗法之后,我的梦想慢慢熄灭了。当面对现实,我开始明白:泰瑞克 的状况将会持续终身。
不幸的是,家是让我感到最孤独的地方。长话短说,泰瑞克 的缺陷 带来的压力,加深了我和他妈妈之间的其他矛盾,最终导致了离婚。在几年来努力尝试共同面对之后,还是觉得独自承担会更轻松一点。我成了一个分担抚养权的单亲家长 ,人生道路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从来没敢想过,也从来未曾预备的事情。
只要醒着,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因为泰瑞克 很少踏实睡一整夜,所以我总是疲惫不堪。睡眠不足一直持续了七年多,而那种疲劳的感受在我身体里待的时间甚至更长。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儿子就像个永动机,跟着他、追着他的时候 ,你很难预料将会出现什么。屋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做足保护措施,就连冰箱、抽屉、马桶都必须上锁。
由于泰瑞克 不知危险,所以我时刻担心他会跑到马路上去、烧到自己的手,或者失足掉进深水池。我对泰瑞克 曾寄予过的梦想,实现了的只有一点——他的确跑得很快,但很不幸,这让我几乎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有一次,他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了。在找寻他的路上,我害怕极了,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最后我在几个街区外的操场上找到了他,那个地方与我们家相隔几条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找到他时他玩得正开心,但我的心仍然突突不停乱跳。或许相比于被诊断为自闭症 ,他的死亡是唯一一件令我更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决定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这让我能继续走下去。心理治疗是当时我能为自己做得最好的事情了。我出生在一个不太会表达情感的家庭,但现在我需要表达情感的能力。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我将情感表达出来了,但要理清这些情感却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被泛滥成灾的情绪淹没了,常常会有很失控的感觉。
我为什么就是平静不下来?专家们总是强调要为泰瑞克 多付出,但这根本无法让我平息愧疚、产生接纳。不能接纳儿子这个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像是有毛病。难道我是个坏人?为什么有了爱还不够?
就在那时(算起来距今已有25年了),我的同事兼好友辛迪 给我看了一篇发表在《咨询与发展期刊》当月刊上的文章,名为《缺陷 儿童与家庭》。那篇文章讲的是缺陷 儿童父母所经历的哀伤,作者是匹兹堡大学的米尔顿·塞利格曼(Milton Seligman)博士,同时也是一个成年缺陷 孩子 的家长 。在慢慢阅读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
许多零碎的情感和思绪开始变得清晰。读完全文之后,我坐在办公椅上向后靠去,缓缓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意识到:“是的,泰瑞克 的生命对我而言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失去孩子 的家长 。”我正在经历失亲的哀伤——这是我给自己下的诊断。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我换了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经历,这帮我学会应对自闭症 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期间我也得到了不少帮助。我终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感了。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社会普遍缺乏对缺陷 儿童父母的支持,对他们所经历的伤痛也普遍缺乏理解。到现在,这种缺乏依旧存在。这也是促使我以心理咨询、演讲、写书作为自己工作内容的原因。
我曾经挣扎在无边的黑暗里,但终于还是找回了自己的人生。那位给我看文章的朋友,她鼓励我开口诉说,并倾听我所说的一切,不带任何评判和预设。辛迪 最后成了我的女友,又过了几年我们结婚了。生活果真携着新的梦想继续上路了。
在我充分认识到儿子的缺陷 会终身存在之前,就已经进入天普大学心理学系开始攻读博士了。我心里知道,泰瑞克 会希望我去追求自身发展,因为我已经为他竭尽所能。那段时间我经常遇到重重的困难,好在学校老师和单位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于是在生活上、职业上,我都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当女儿开始认字的时候 ,我感到特别欣慰。她每学会一个新词,都是在向我昭告:她的大脑是正常的。看着她学着辨识文字,我不禁喜极而泣。这个阶段让我无比振奋——更不用说,当知道她能正常学习时,我有多么宽心了。
我真是连呼吸都畅快起来了。人的正常发展看起来像个奇迹。我大女儿在美术和写作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每当她给我看她画的画、写的文字的时候 ,我的心里都充满了自豪与感恩。因为我已经明白,有时候 生命格外脆弱,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的心会被某个东西击碎。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家有缺陷 儿,如何顺利应对。这个过程的关键是韧性与平衡。我的研究兴趣不仅仅来自于想更多地了解自身,我更希望我所学到的内容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我希望能在家庭成员和专业人员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在泰瑞克 过完九岁生日过后,我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向家长 、从业者团体作演讲,并成功地帮助人们沟通、合作。那个时候 ,泰瑞克 的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全天候陪护的程度,我不得不让他住进专门机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在第十三章我会更深入地解释这个决定。1990年,我受邀参与一个项目,帮助新泽西州教育部研发一套培训体系,旨在促进家长 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后来我成了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培训师。在将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相结合的方面,我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各种学前项目与专业会议上,我总共向数千家长 和业内人士作过演讲。通过这种方式,我与泰瑞克 同在,并且找到了某种意义。
1991年,《咨询与发展期刊》发表了我的文章《失去的梦想,新生的希望》,讲述了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对我职业道路的影响。读者纷纷给我发来信件、打来电话。有大学教授说,他们使用我的文章作为咨询课和特殊教育课上的下发资料。我听了之后感到特别欣慰。
同年,我和辛迪 的第一个孩子 卡拉出生了。过了两年多,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 ,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佐伊。卡拉和佐伊的成长,见证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活力。1992年,辛迪 和我创建了独立心理咨询室“新选择”。后来我们的咨询业务发展得很好,于是我辞去了在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工作。现在我专职服务于自闭症 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孩子 的家长 。我和辛迪 一直都围绕着我们的家庭来安排工作,这是我们俩都喜欢的一种生活。
此外,我还担任了一些学校和家长 团体的顾问,其中包括一个隶属于“先机计划”(Head Start)的三年期特别项目的心理顾问,该项目旨在增进父亲及男性榜样在幼儿生活中的参与度。目前,我为家庭提供咨询,并在国内外开设讲座。我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谋生,这是一种特别的恩赐,也是我感到特别自豪的事。
这一路走来,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儿子的异常对我成长的帮助,是我过去不曾料想到的。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做不寻常的事情。我从中汲取的知识与智慧,仍在帮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泰瑞克 让我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他如此天真无邪,大部分时候 都很快乐。他这样一个温柔的生灵,无论在哪个机构,都受到工作人员的喜爱。仅仅想到这些,就足以让我安然、微笑。
我现在的生活不同过往,却充实满足。我一边帮助其他自闭症 家庭,一边不断学习。有时候 我想,自己何德何能,值得拥有如此丰富的人生。每当我走进一家早期干预机构,或者开始为新确诊孩子 的家长 做一场咨询,我都会重温自己的经历。当我反观自己的内心,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就会减轻。他们的故事提醒我,我有资格感觉良好——因为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本书的焦点是:孩子 被诊断为自闭症 之后,如何在这个持续困扰终生的过程中去关注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我的目标是整合自己的个人经历、临床经验、研究与实践知识,去跟与我境况相似的家庭成员对话。我帮助家长 理解自己的思维情感,从现状中寻找幽默感,坚持不懈地爱孩子 、帮助孩子 成长,并使家长 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力量。每当做到这些的时候 ,我都会感到我的工作是成功的。
标签
陈力爱玲
初中三年级
2021年08月19日
情感之旅
--- 美洲原住民谚语
到了四岁的时候,史蒂芬还是不会说话。他在书中回忆说,那时,他在家里总是被当做一个完整饱满的人来对待。现在,史蒂芬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纽约长岛的阿德菲大学担任特殊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
本帖最后由陈力爱玲 于2021-08-19 10:19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