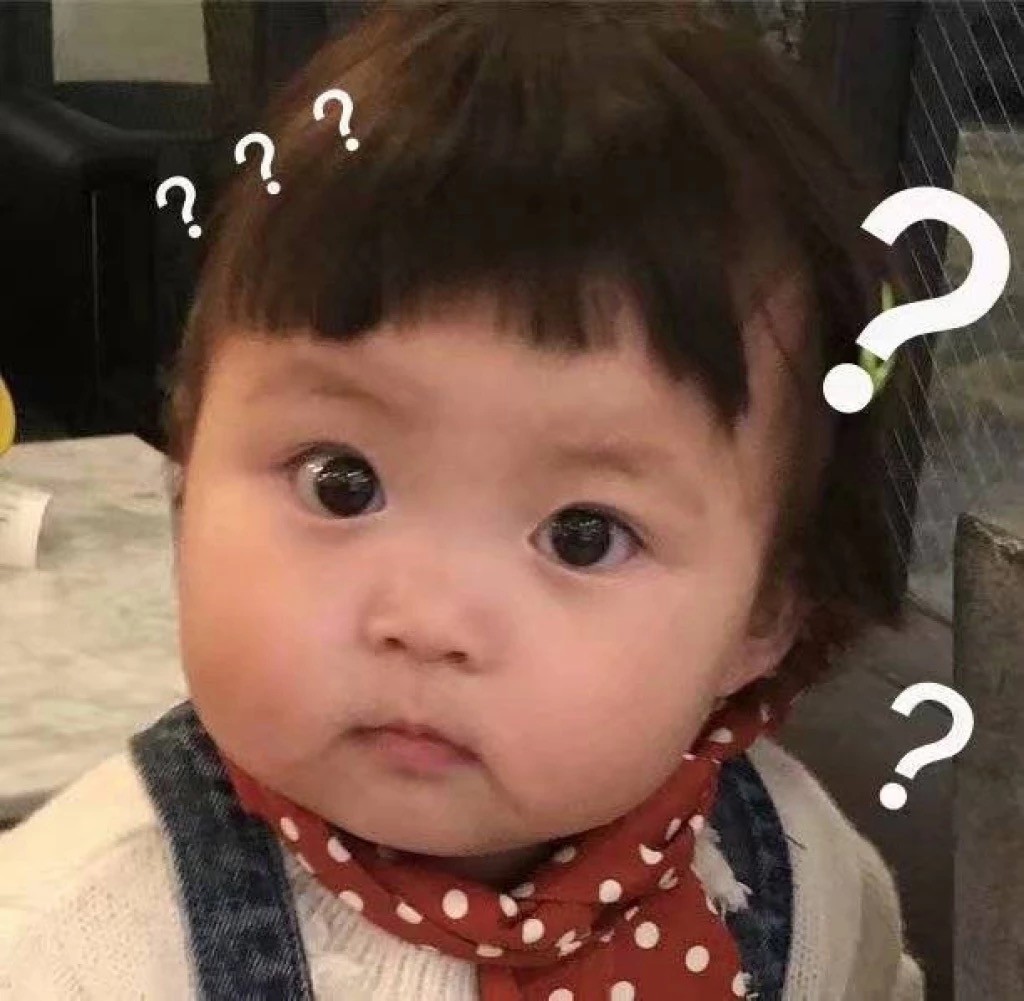这两天因为在微博上看到医患矛盾的争吵,突然有感而发说起16年前的朱令事件。这件我努力过的事情,并没有像小时候听的童话那样有个美满的结局,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面对。现在想想,还是应该趁大脑排除痛苦回忆的机制彻底发挥作用前,把当年的事情记述下来。
这篇文章没打算说明什么,只是帮助自己记忆,所以可能拉拉杂杂记述了很多琐事。这么多年我的记忆也可能出错,我只能保证我是诚实的记述,欢迎知情的朋友补正。
对于朱令事件Z简单和准确的概要请见维基百科:
关于朱令事件的各种传闻和材料可以参看:
http://www.huaren.us/dispbbs.asp?boardid=331&id=891136&page=1&star=1
朱令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在初三同班过一年,我对那时的记忆好像只有她是个很正派的女同学,有次政治考试我撺掇她打小抄对答案,她很不情愿答应了,过程那叫一个手忙脚乱,事后也严词拒绝再干这种事了。然后的记忆就跳到她姐姐随北大同学出去爬山意外身亡,这个活泼的女孩子沉默了好几个月,后来虽然恢复了但总有些不同。
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成为学校里特立独行的典型,让老师头痛的对象。她虽然不是班干部、三好学生那种类型,但至少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们似乎没什么交集也没有来往。然后我考上了北大,她考上了清华。
印象中在她出事前,我只在去清华找朋友玩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一次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是95年的寒假,同学聚会时听到有同学说“现在怪病真多啊,你知道朱令突然肚子痛住院,然后头发掉光了,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然后听说她出院回家休养,然后是95年4月初的一天,再次接到那个同学的电话。
“你是不是去看看朱令,她好像不行了”
“不是已经好了,在家休养吗”
“不是,又发作了,而且这次很严重,已经在协和的ICU病房昏迷了”
我们一群同学约在周六去医院看她,那年我21岁,同龄人的死亡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朱令静静的躺在ICU病房里,身体半裸着插满了管子,因为卫生的要求每次只能一个同学进去看。轮到我进去后站在她的病床前,不知道怎么我先不吉利的想到了这很象向遗体告别,接着意识到这是一个同龄人处在垂死状态,忽然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恐惧感想要拔腿逃走,但是双腿又像灌满了铅逃不掉。好不容易磨蹭够了觉得不失礼节的时间走出ICU,坐到她父母边上,看着悲哀的老人年少的我就在想赶紧编点什么安慰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听同宿舍的蔡全清讲过他替系里的陈耀松教授打杂好像在搞一个叫什么Internet的东西,可以和全世界联络。于是就没话找话的跟朱令的父母说有这么个东西,没准可以向全世界寻求一下帮助,她的父母将信将疑的把病历复印了一份给我,还记得我正要走那个同学跑出来叮嘱我说“贝志城,你一定尽力想想办法”
回到家里我很快把求救信写了出来,当时我想老美Z爱谈民主自由,我得把救人这事跟这方面扯上他们才会重视吧。于是我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梦想的地方,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虽然中国Z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尽了Z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诊断她是什么疾病”,之后是照抄病历。找到一个美国朋友翻译成地道的英语,我拿着它去学校和蔡全清一起去系里的机房在四月十日周一晚上发出了这封求救邮件(当时是向两个类似BBS的学术网络Usenet和Bitnet所有跟医学相关的群组发出的),很快第一封邮件回来了,是个爱尔兰人说他会为朱令祈祷,接着第二封,说怀疑是一种叫“thallium”中毒的病;然后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回信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也有Internet了,他们会帮忙把信转发给他们周围认识的医生或者他们的导师。那天我头一次感受到Internet的力量,看着邮件不断在Unix绿终端屏幕上跳出,兴奋的一直待到早上五点,才把受到的近百封邮件拷到软盘上带回宿舍。
记得那时候中国的Internet只有三条256K的链路,分别在清华、中科院和化工大学。我们能蹭上完全拜托我们力学系在北大校外靠近清华院墙,据说是陈耀松教授自己搭梯子从清华墙那边接过来一根线。后来我们产生了惊人的流量好像还让陈教授个人掏了腰包,在系里有人质疑学生怎么私人和国外大规模联系时也是陈教授挡回去的(他说学生就是帮帮同学嘛),这些我一直感念。
回到宿舍我们先查了字典,原来“Thallium”是“铊”的意思,当时我们面对是问题是从Unix终端下来的邮件会整体打包成一个大文本文件,在电脑上无法阅读。这时候同宿舍的刘莅(他是我在大学Z好的朋友)主动请缨,用微软的Access写了个软件,先把邮件拆分成一封封,然后把邮件标题、发件人摘出来存进数据库。之后同宿舍的王惠文也加入了,我们一起完善程序,可以输入发件人的职业(医生、认识医生的热心的中国留学生、打酱油的等等)、统计一个发件人发回的邮件数量,这样设立一个权重打分机制决定我们要特别优先给谁回信;同时把比较多提到的关键词铊中毒、格林—巴利综合征、莱姆病等作索引,看分别有多少人提到,关于任何一种病从朱令的家长那里听到说法就会回给提过这些病以及被标注为医生并比较热心交流的人回信。然后宿舍里英语Z好的吴向军也加入进来帮着一起浏览邮件。事实上,到朱令确诊前的这十来天我主要是在外面跑,而他们则一直经常通宵看邮件修改程序。有这样的同学和陈耀松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直为北大而骄傲的原因。
之后我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我被母亲的带着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一位和蔼的老人。她听完我的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大意说这个女孩的病好像协和也很重视,现在有群年轻人用了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
大概也就在13、4号,我们有了一定的邮件积累,上面猜测了各种可能也提了一些检查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几乎看不懂)。我给朱令的父亲打了电话,其他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记得我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时,他轻轻的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已经排除了。